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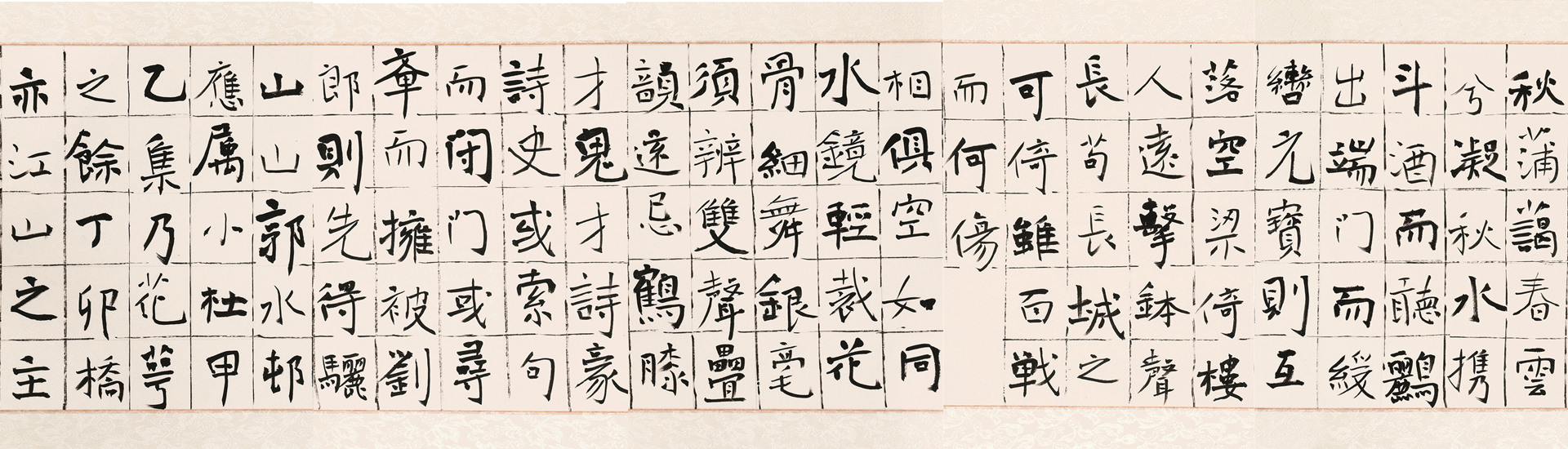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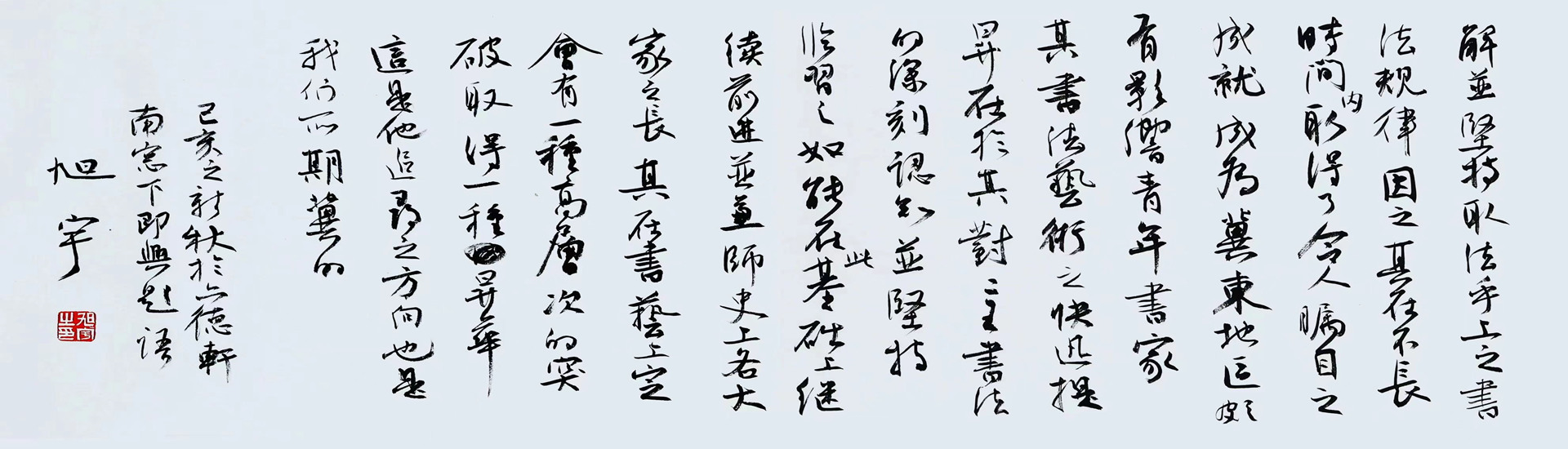

在我书房的南窗下有一方桌,上有一座墨绿色顶戴黄冠的浑厚雅石,常成为友人们的谈资。两侧置二把椅子,来访者便在此品茗聊天。兴之所至,上溯老庄,下到现实,云高地广,无有尽头。而本人年纪较长,朋友们又常请我胡侃。其间,因受友人启示,难免有些新意脱口而出,给友人些许感受,于是大家忽悠我将这些新意感受整理成文章,与众人同享。也正巧合,去夏《当代人》杂志增设谈艺版面,他们提出要为我设个调侃的所谓“旭宇艺术大讲堂”专栏,每期刊发拙文两三篇。这给我出了难题。我已是年近古稀之人,眼花手拙,写这样的稿子,实在有点儿逼上梁山,可朋友却建言:“将你聊天的内容整理出来不就行了。”于是,“艺术随谈”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炉了。
这个专栏虽是逼上梁山之措,但也确实让我有机会梳理了几十年从艺的思情,尤其是自青年时期开始的老庄思想的研习,在有意无意间形成了我的艺术观。这可能有些偏颇,甚至不与当下时令的躁进和张扬合宜,但也绝是我的善意直言。中国传统文化教我与人为善,吾信守之。但是一个最善意理念的提出,也可能无意间伤及了持不同理念的人们。学术问题就是要坦诚,以无私去扣问真理。
在我整理文章的困难时刻出现了一个机缘:去年的新文人书家会议上,我省著名文艺评论家郗吉堂同志主动提出要为我做整理文章之事,并说二十年前慕名于我,想为我做些事情。这使我非常感动。
我相信缘份,认为它是生命体的一种天然的契合。与吉堂同志的不期而遇,使我完成了一年期的专栏文稿,这更让我坚信此理。而编发我十多篇文稿的郭文玲女士的认真作风,也让我受益匪浅。
“艺术随谈”成书之后,我的老友著名文艺评论家丁国成先生写了序言,河北教育出版社编辑徐占博小友肯定拙集,提出要写篇后记,我建议将他的编后也作序言付梓,以便读者在开卷时了解我的初衷,并渴望得到指谬。
我南窗的书桌上摊开着《旭宇艺术随谈》的设计大样,有阳光洒在书稿上,而窗外的石榴花正在开放。秋天,它丰满而清甜的果子将见证这本《旭宇艺术随谈》诞生的历程。
亲爱的读者,缘份是一种天机,愿您打开这本书的时候,不经意间也有一树榴花开放,和您一起在我简陋文字的行间行走。
旭宇 2009年5月于南窗